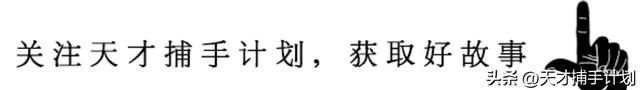
这个有点疼的故事,不是身体疼,是心疼。
2011年,刑警陈文章遇到了那个让人心疼的女人,当时她正躺在稻草堆上,她身上的痕迹,陈文章看了一眼就哭了。
在此之前,她曾被丈夫常年家暴,高位截瘫。
陈文章说,他记录这起案件,不是为了让人看到这个女人有多惨。他想要去记录,去解析这类事件发生后,我们可以为当事人做些什么。
“只有这样,悲剧才算是有了意义,不是吗?”

初七是上弦月,山野的空气特别好。
我和队长、法医几个人一排坐在帐篷前。队长找了些干柴点火,法医在勘验车上找出他的私货,一瓶高度白酒,我们聚在火堆前饮酒取暖。
我甚至以为这是一场篝火晚会。
如果不是帐篷里还有一个女人正在腐烂的话。
树丛中,闻到腐臭味的野狗久久不肯散去,绿色的眼睛像萤火一样闪烁。
队长知道我从不喝酒,但还是给我用纸杯接了一点白酒,让我驱驱寒,喝完心里好受一些。
我接过纸杯一饮而尽,眼泪也掉了下来:“都怪我,还没抓住马成功。”
队长没有安慰我,甚至没有看我,只是和法医一口一口抿着酒。
那是2011年3月11日,我当刑警的第一年,我负责的第一起案子的女事主。我曾答应过她,一定把人抓到,一定给她公道。
那时候她的脸颊还是淡红色,低着头,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麻烦你了。
而这一刻,凶手还没找到,她却慢慢失去生命体征。就在我身后,在那个昏暗无光的帐篷里。

三个月前,市里发了一起疑难命案,整个刑警队焦头烂额。
刚弄到点线索,派出所又报上来另外一起重伤害案件,据说当事人是个高位截瘫的女人。
侦查员们正打着鸡血要拿杀人犯,这时要把谁换下来干这种“小案子”,人能掀桌子。
队长在办公室里瞅了一圈,盯上了我这个刚工作一年的“大茶壶”。
队长给我说得很好,说我来了快一年,在专案组端茶倒水订盒饭,还不如试着自己办一个案子。要是办好了,以后就让我当主办侦察。
我想想也是,万一能弄到个大案呢,痛快地接下了这个大家都看不上的案子。
我只知道是医院报案,三天前有个男人送来了一个颈椎骨折、昏迷的女人,交了一千元住院押金后就跑了。
医院抢救了很久,人算是救活了,但落下了一个高位截瘫。
苏醒过来的女人对自己的身份、受伤的原因都绝口不提,医院没法强迫,于是报了警,想要警方找个人给她负责。
走进病房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,觉得这个女人看起来状况不差。
虽然重伤瘫痪,但女人脸色不坏,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口,穿着病号服很干净,对比刑警每天见的那些血呼啦呲的,可以说是很平和了。
我给她自我介绍,又问了几个问题,她都不说话,甚至一眼都不看我,就盯着天花板。
于是我告诉她,我已经查到了那天送她来的人叫什么名字。
这个女人一直不配合调查,可能是袒护伤害她的人,也可能就是意外受伤想赖医药费。
这种情况我问也没用,所以提前就去查了查送她来的面包车,发现车主名叫马成功,45岁,已婚无子,妻子叫做邓娟。
当时是2011年,一代身份证还没有作废,网上查不到马成功和邓娟的照片,无法确认受伤的女人是不是邓娟。
我只能去当面诈她一下,果然,女人听到马成功的名字,眼角似乎抽搐了一下。
我心里有了底,直接叫出她的名字:“邓娟,你的伤是怎么回事?”
女人不作声,但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
不知道是泪水留在脸上让她不舒服,还是其他的原因,她努力摆着脑袋,想用枕头蹭掉脸上的泪水。
这个对普通人再简单不过的动作,她却做不到。
这一刻我才想起,她是个高位截瘫的病人。
我赶紧扯下纸巾,帮她把眼泪擦掉,安抚她说,如果有人对她施暴,我绝不会放过他。
她终于看了我一眼,含着眼泪说了第一句话:“伤是马成功打的。”

邓娟告诉我,三天前,是她和马成功离婚案子开庭的日子。
开完庭后,她被马成功在法院门口堵住了。
马成功要把她拖上面包车,两人在车前扭打起来,她被马成功按到座椅下面,又挨了几脚。
邓娟只记得当时一阵剧痛,醒过来就在医院了,下半身也没有了知觉。
面包车谁都见过,后排座位底下不到30厘米,邓娟身材高挑,要塞进这种地方,人对折过来也不够。
多半是扭打中撞到了颈椎,一骨折就是个高位截瘫。
很显然,这就是个故意伤害的案子,离婚纠纷,再常见不过。
不是大案,我心里失落,但想到是主办的第一个案子,真得好好办,把这个马成功逮回来。
没想到案子小办起来也不方便。
我去开伤情鉴定,法医说还在做命案的尸检报告,再等等才行。
我也理解,命案总比重伤害大,只能自个儿去马成功和邓娟的家里蹲人。
蹲了两天,啥也没捞到,临走的时候我又在他门上插了一张小广告卡片。
一个星期之后再过来看,小卡片依然没有动,我知道马成功短期之内不会回来了。
我去了马成功的老家,又是看了好几天监控追查他的车,又是把他的身份证上网追逃,全是徒劳无功。
这怂硬是车也不开,身份证也没用,人间蒸发了。
转眼到了过年,所有警察都被调去巡防维持秩序,忙到元宵节后,半个月积压的案子堆上来,整个警队一下四脚朝天。
我再没精力去追捕马成功,只是偶尔想想,这家伙到底长啥样?他到底哪天才要用身份证?
等我把他逮住,非得给他扭到那家医院,让他给邓娟道歉,端屎端尿去。
于是,马成功的卷宗和许多积年逃犯的一样,被放进了黑漆漆的案卷柜。
我再听说这起案子,就是一个陌生来电,邓娟的哥哥邓秋生告诉我们,她快死了。

我们到达邓家村的时候,天刚刚上了黑影。
这是个山凹子里的小村,进村只有一条路,邓秋生早就在村口迎着我们了。
他穿着很朴素,个子不高,说话时有些畏畏缩缩,没寒暄两句,就带着我们往村子外走。
我问他邓娟到底在哪?
他说,在村外的机井房里。
机井房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拿来放灌溉井的地方,盖的时候就没想过遮风挡雨。
几十年过去,门口的草长了齐腰高,墙面斑驳,只有一间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野地里。
越走近那个屋子,越闻到一股臭味。
我推开漏风的门板,腐烂的恶臭差点把我的早饭顶了出来。
邓秋生跟在我后面往墙角一指,说,这就是邓娟。
屋子里没有电,点了一盏豆油灯,昏黄的灯光被我带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欲灭。
借着那一点光,我勉强看清墙角的稻草堆上有一团被子,被子下似乎是个人形。
法医过去掀开被子,我听到了他呕的一声。
被子下的,与其说是个人,我宁可相信是个尸体。
一头乱发遮住了脸,厚厚的棉衣上都是脓和血的痕迹,身体似乎已经腐烂了很多地方,只有眼睛还在微微地转动。
法医手电照着的地方是她的脚,脚趾少了好几根,伤口还是新鲜的,在流血。

“怎么回事?”队长指着邓娟的脚趾问。
邓秋生捶打着自己的头,低声呜咽起来,并不回答。
“到底怎么回事!说!”
“被老鼠啃了。我们也没办法天天看着她。”
邓秋生说,我把案子办下来后不久,医院也知道了邓娟的身份,联系了他们去缴医药费。
当时他们都很惊讶,家里嫁得最好的一个姑娘,没想到有一天出这种事。
邓家一家有四个兄弟姊妹,数邓娟最聪明,从小成绩好。
打小邓秋生就知道,他要挣钱供妹妹读书,等妹妹长大挣了钱,嫁了好人家,他也能有好日子过。
可偏偏到了中考那一年,妹妹突然喜欢上了外村的一个混子马成功,铁了心不读书了,要跟他结婚,进城去“闯荡世界”。
刚一结婚,小两口就搬进了城里,不回这个又穷又破的邓家村了。
最开始几年,邓娟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,穿得也比他们这些乡下人时髦。
95年春节的时候,马成功不知道在哪弄了一辆天津大发,拉了一车的年货回村,村里的小孩围着车又摸又跳。
有那么一瞬间,邓秋生觉得他这个妹夫还不错。
妹妹越来越少回家,每次回来都愁容满面。有那么一两回,他甚至在妹妹脸上看见了淤青。
就像她突然提出要嫁给马成功那样,有一天,妹妹突然开始闹离婚了。
在他们这个小山村,连离婚是什么都没听说过。
更何况,这几年爸也去世了,妈也老了,几个兄弟姊妹各自成家,邓娟要是离婚,连个家也没有,该上哪去?
他也劝邓娟,当年俩人不是那么好,到底出了什么事过不去?离婚这种事,我们这种人家闹不起的。
邓娟不回答。
没成想再收到消息,已经是邓娟离婚失败,被打成了瘫痪。
而离开医院后发生的事儿,更是让我听得头晕目眩。

邓娟账上一分钱也没有,大概早被马成功转走了。
一家兄弟姊妹一块凑钱,ICU一天好几千,加上手术住院的钱,几兄弟的钱都花光了。
妹妹必须出院,可是能放到哪儿?几兄弟家里都是手停口停,照顾她,就是饿死自己孩子。
最后,邓娟又被送回了老家。
七十多的老母亲,端饭碗都手抖,根本没法做翻身擦洗的活儿,眼睛都看不清女儿生的褥疮。
但邓娟也已经感觉不到,她的脖子以下什么知觉都没有,只有两只眼睛还能活动,醒着就看着天花板。
她很少哭,也很少和母亲说话。
高位截瘫是不致命,但对于这么穷的家庭来说,它比人死了还残忍。
到后来,邓娟身上的味道实在太大了,村长找上门来,说人不能死在屋子里,不吉利。
别人家都是弄个板房,或者送去医院,邓秋生去求村长,最后求到了这间机井房。
母亲每天颠着小脚、举着一盏油灯去送点吃的,过了有一阵子,才发现去的时候会有老鼠从女儿身上爬下来。
摸一摸脚趾,已经少了好几个趾头。
邓秋生走投无路,到处托人去给马成功带话。他说好赖是你老婆,人都快不行了,能不能回来看看?
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,马成功真的来了。
他约在了正月十五,警察都去晚会上维持秩序的日子;又从上午拖到傍晚,还多花了一个多小时绕了后山一条小路,在暗处观察着邓秋生,怕有埋伏。
邓秋生是个地地道道老农民,有什么都写在脸上,就是眼巴巴地望着进村的土路,一脸的苦。
马成功看了半天,才晃晃悠悠地从草丛里走出来。
邓秋生吓了一跳,赶紧赔着笑脸,掏出早上就买好的紫兰州,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支递给他。
马成功瞟了一眼,没接,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吉祥兰州点上了。
邓秋生讪讪地把烟又塞了回去,搓了搓手,终于开口问他,是不是得把邓娟接回去照顾下?
马成功哼笑了一声,说最近有事,忙不过来。
邓秋生难堪极了,想来想去,又求马成功要不去看看邓娟吧?
他喋喋不休的,马成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,只能答应。
一走进机井房,他就厌恶地捂住了口鼻。
昏黄的灯光下,老妇人正在用勺子给女人喂水。
女人抬眼看见了他,立刻紧闭嘴唇,直勾勾地盯着他,任凭勺子的水流入她的耳后。
那种目光不知怎么迅速惹恼了马成功,他一口浓痰吐在邓娟身上,张口就骂:“看你冤得很嘛,来给我再打一顿!”
说着他就要踹邓娟,邓秋生赶紧拦住了他,连推带搡把马成功弄了出去。
马成功骂骂咧咧地走了,这一走,邓秋生就再也没见过他,任凭他怎么找人捎话,马成功也不回应。
一个多月后,邓娟昏迷的时间越来越多,水米不进,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有人告诉邓秋生,你家这个案子报过警,是不是得找警察来看看?
我来了,我看着躺在稻草堆中的女人,什么也做不了。
我之前就曾经隐约想到过,马成功没到案,就没人给邓娟补偿付医疗费。
我还曾经为这跑了一趟医院问能不能申请特殊医保,被骂了一通。接着又去了民政部门,还是没有结果。
工作人员劝我说,邓娟这个情况,再治也不可能站起来了,就让她家人照顾着,护理病人也不花几个钱。
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说得对。
我觉得我尽全力了,抓捕马成功,能做的我都做了,做不到的我也没办法。
但现在,看着眼前的女人,我有股热气往脑袋上冲,我控制不住地大喊大叫,要叫救护车。
队长直接摁住了我。
邓秋生说救护车已经来过了,不肯拉人。
法医也在旁边说,是没救了,肚子上烂穿的窟窿都能看见脏器了。
最后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,搭把手,给邓娟换个地方,至少别让她死在这个垃圾堆。

我们从车上拿了法医的尸检帐篷,在机井房旁边的荒地里架起来。
法医用被褥包好邓娟,我们再小心翼翼地把她抬上担架床,放到帐篷里。
刚安置好邓娟,我就看到不远处的黑暗里有幽绿的目光闪烁。
是野狗,它们不知从哪里嗅到了死亡的气息,有几只胆子大的甚至跑到了帐篷跟前。
我捡起石块砸过去,野狗吃痛嗷的一下,跳到了一边,对着我一阵狂吠。
旷野里“砰砰砰”三声枪响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队长开枪,居然是对着狗开的。
被击中的野狗一瘸一拐地跑开了,剩下的野狗也四散开去。
队长放下枪说,我们恐怕得守一晚了,不然她会被野狗吃完。
这一夜太长了,我甚至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。抓捕马成功吗?
他明明是这次惨案的元凶,还仍然在逃。
但邓娟的死因大概率是恶性褥疮感染引起的并发症,马成功可以狡辩自己只踢了她一下,一切与他无关。
我要怎么做才能给他定罪?怎么才能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?
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,几乎没说什么话。
队长也给邓秋生倒了半杯,他拿着纸杯很惊奇的样子。队长笑笑说,我们也喝不完,剩下的你带回去。
邓秋生瞪大了眼睛,看着那杯酒,抿一小口,又看看酒瓶中剩下的量。
我们再想给他续杯,他不要了,一直盯着空了一半的酒瓶。
我们喝得更慢了。
邓秋生不时进帐篷去看一眼邓娟,后半夜突然有一次慌慌张张地冲出来说,妹妹醒了,她要喝水!
我有点怕被她看到,怕她问我马成功抓到了没。
法医在旁边摇了摇头,小声地说道,这是回光返照。
邓秋生用纸杯给她嘴唇沾了沾水,邓娟轻轻地说:“哥,芬芬该放学了,我要去接她。”
邓秋生满眼是泪,哽咽着回:“天还没黑,芬芬还没放学。”
邓娟懵懵地哦了一声,又嘱咐邓秋生,一会让马成功去接芬芬吧,“我累了,想再睡会。”
说完,她又陷入了昏迷,留下邓秋生失声痛哭。
我从来没有听过芬芬这个名字,问邓秋生那是谁?
邓秋生回答说,那是邓娟的女儿,但这女儿一年前就死了,跳楼自杀,邓娟也是从那天开始突然铁了心闹离婚。
我追问邓秋生,知不知道外甥女为什么自杀?
邓秋生说不知道,只知道那之前这个外甥女就有点叛逆,离家出走过,说是挨了马成功的打。
有没有可能,芬芬是被家暴后激愤跳楼的?
邓娟的案子治不了马成功,有没有可能马芬芬的死可以给他定上一个虐待致死?
我像是抓住了一根稻草,一直念着“马芬芬”。
邓娟离婚的原因,这个家庭里的暴力、愤怒、绝望,伴随着死亡尘封下去的秘密,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孩子找到谜底?
那时候的我,一心要证明马芬芬的死与马成功的家暴有直接关系,要借此让马成功罪有应得。
但没想到等待着我的,是一封让我记了十年的遗书。

邓娟最终在天亮之前停止了呼吸。
我们按流程做了尸检,把人送到殡仪馆。
尸检会把人的衣服都剪破,必须重新买寿衣。邓秋生不知道,临时捏了一把钱去殡仪馆门口,又空着手回来,说钱不够。
我们几个小警察,凑了三百来块钱,买了从头到脚一整套的寿衣。
一口薄棺,邓娟被带回了家,连葬礼也没有。
我当天就开始重查邓娟女儿马芬芬自杀的案子。
我从马芬芬的学校找到她的老师,又找到了她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小陈。
小陈一听我问起马芬芬,立刻问道:“警察叔叔,你们是来调查芬芬的死因的吗?”
我心里一拧,问她为什么这么说?
她说,因为芬芬自杀前曾经跟她说,要让她爸爸付出代价。
在小陈眼中,马芬芬最初是个很孤僻甚至有点危险的女孩,她常常带着伤来上学,有时眼角一块淤青,有时一瘸一拐的。
同学们都传她是坏女孩,经常和校外的人打架,也有人说她不听话才被父母打成这样。而马芬芬的沉默,就像是一种默认。
但在小陈第一次来月经弄脏了衣服的时候,是这个从没跟她说过话的女孩站了出来。
马芬芬把自己的校服系在她的腰上,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了厕所。
小陈说起这段故事,几乎泣不成声。
在那之后,她们渐渐成了朋友。小陈鼓起勇气追问芬芬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,才知道那是她爸爸打的。
没有为什么,只是因为他今天回来,很生气。
小陈说,那天芬芬说着自己的爸爸,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。她想摸一摸芬芬被打肿的眼睛,可是被一把推开了。
“她把敷伤的鸡蛋一口吃掉了,扶着栏杆告诉我,要是跳下去就解脱了。”
“当时把我吓坏了。我抱着她,让她不要想不开。“
"然后她笑了,她说是骗我的,自己还有妈妈,就算为了妈妈也要好好地活着。”
“她还说,上了高中就解脱了,以后上完大学就把妈妈接走,找一个她爸爸找不到的地方好好生活。”
芬芬曾经愿意忍耐,做好了长久的计划,想象着未来的生活。她不应该会自杀的。
但那年年底,马芬芬突然好几天没来上课,据说是请了病假。
那时候功课很紧张,轻易不会请假,小陈担心她是出了事,就趁着自习课逃了两节课去她家看她。
开门的芬芬脸上全是伤,嘴角还有血。
小陈劝她报警,她没说什么,还说过几天她脸上好些了就回去上学。
就在几天后,她放弃了这所有的计划,跳楼了。
跳楼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?马芬芬长期受到家暴这件事,辖区真的没有人能管吗?
我回队里找队长求情,求他至少给我个介绍信,让我去问问芬芬自杀那天出警的警察。
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芬芬一身的伤,有没有看到马成功长期家暴这对母女的痕迹,他凭什么把这起自杀草草结案?
他知不知道,如果他再多问一句,真的有可能救下一条人命?

我见到了那天出警的警察小孙,一个比我还年轻的小警察。
小孙为人不坏,听说我来调卷,一点也没有刁难人就在那帮忙找,还跟我热络地闲聊。
但档案找到后,我有点说不出话了。
那根本算不上档案,只有一张报警登记表和一份询问笔录。
根据记录,芬芬跳楼当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,邓娟是后来赶回来的,而马成功直到警察离开都没有出现在现场。
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,芬芬的死被定性成了一场绝对的自杀,简单结案。
我问小孙对当天的事情还有印象吗,他啧啧了两声,露出惋惜的表情说,太惨了,第一次见到跳楼的死人,还是个初中生,人都摔得不成形了。
我又问他,当时调查死因了吗?
小孙含糊地说,父母管教严格,可能动手打了几下,小孩子就想不开跳楼了,又抱怨现在小孩子心理素质太差,父母打几下就能寻短见,太不负责了。
我抬高了声音,问他真的问过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吗?
小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,说当时女孩妈妈抱着女孩的尸体哭昏过去了,我总不能往人伤口上捅刀子,问人家女儿怎么死的吧?
我好像看到了抓不到马成功的自己。
所以我更清楚,不是不能查,只是真的觉得这件事不够残酷,不用那么上心。
我掏出关于小陈和邓娟的档案,让他自己看。
小孙看得脸一阵红一阵白,看完了,他也明白了,我现在是想办马成功没有由头。
他问我他还能帮点什么?
我说查查芬芬生前有没有家暴报警记录吧,我们要证明马芬芬跳楼是被虐待致死。
出乎我的意料,芬芬和邓娟都没有因为家暴报过警,倒是查到马成功的邻居有几次举报马成功住的402噪音扰民。
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,我们敲开了邻居的门。
我没想到,这个陌生的邻居宋大姐,竟然是唯一知道这段婚姻里发生了什么的人。
宋大姐说,楼上这一家刚搬来的时候,就已经有些不对劲了。
那时,马成功还整天打扮得很体面,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包,整天举着个电话吆五喝六的,走起路来像一阵风。
而女主人邓娟则完全相反,身材高挑漂亮,却永远穿着过时的衣服,遇见人总是低头走过去,手上把拎着的菜换到没人的一侧,眼神中充满了戒备。
一家三口搬过来没几天,她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,男声疯狂地咒骂着,伴随着小女孩凄厉的哭叫。
想起小孩每次见到她喊阿姨好那个乖乖的样子,宋大姐有点心疼,上楼敲了门。
她也就是个独居女人,但马成功一看到她,立马就蔫巴了,嘟嘟囔囔放了几句狠话,就撂下母女出门了。
宋大姐搂住鼻青脸肿的芬芬,不断抚摸着她的头发安慰着。
邓娟抱头蹲在门边,哭不出声音来。
宋大姐和这对母女渐渐熟悉起来,有时候也会听邓娟的念叨——马成功最初是个好人。
宋大姐也知道,邓娟很难离婚,因为这个女人还记着那些日子。

邓娟说过,她是在初三那年,有次参加庙会,遇见了马成功。
马成功正在庙会上卖磁带,穿着一身牛仔装,扛着录音机在庙会上跳迪斯科。
邓娟曾经和他同过学,没想到两年不见,同学变得这么时髦。
马成功热情地和她聊了一个下午,讲他这两年走南闯北的故事,听得邓娟很羡慕。
临走的时候,马成功在摊位上随手抓起两盘磁带塞进了邓娟的书包里。
过了两个礼拜,马成功就找到邓娟的学校里来了,说送了邓娟磁带,忘了她没有随身听,说着又送给她一个随身听。
一个随身听能抵邓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。
她当时不仅是心动,更是羡慕,想知道自己如何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。
她和马成功走得越来越近,也越来越觉得,外面的世界比读书迷人多了。
中考失利后,她索性就不读了,和马成功一起搬到了城里,年纪轻轻就开始一起打拼。
说是一起打拼,做生意的大头还是马成功。他开音像店的时候,四处进磁带谈生意,邓娟就负责算算帐、看看店。
他们最风光的就是开着大发回家的那一年,也是那一年,芬芬出生。
从此邓娟的全部精力就投在了芬芬身上,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
而马成功的生意却越做越差,主营的磁带逐渐被MP3取代,音像店倒闭了,接着办餐饮也失败了。
马成功沦落到了打工搬砖,心里还挂念着做生意的梦想。
两厢不如意之下,所有的怒火都转移到了邓娟身上。
他挑剔邓娟家里穷,不能给他助力;怪她一定要住在城里,还要住学区房,芬芬又不是上学的料,有什么好读的?
这栋楼里也有人打老婆,但没有人像马成功打得这么狠,三天一小打,五天一大打。
一开始宋大姐和邻居们还会去拉架,报警扰民,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少了。
有一天楼上的摔打声结束得特别快。
宋大姐还奇怪马成功今天善心大发了,没多久就听到门铃响了。
邓娟支着一条腿站在门口,脸色煞白,汗水几乎将她的衣衫湿透了。
她说她的腿可能被打断了,想拜托宋大姐叫个医生。
她的女儿芬芬就跟在她身后,死死攥着妈妈的衣角。
宋大姐看得触目惊心,劝她实在不行还是报警吧。
邓娟苦笑一声说,要不是为了芬芬,她早就不跟着马成功了。
宋大姐叹口气,知道她要不这么说,心里也难受。
可那时候跟在后面的芬芬,是怎么想的呢?
芬芬跳楼的那一天,是宋大姐通知的邓娟。
她电话里只说,芬芬摔了一下,要邓娟回来看看。
邓娟赶到小区的时候,现场已经被居民围了起来,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,似乎又在回避她的目光。
宋大姐说不出的心疼,跑过去抱着她,一边哭一边劝她想开些。
邓娟挣开她的手,着了魔一样往血泊里走,捧起女儿摔得不像样子的头,一摸,手上都是血。
她似乎在哭,但发出的只是兽类一样呕呕的声音。
警察来了又走,直到殡仪馆的车都来了,邓娟还是一动不动。
宋大姐帮着殡仪馆的人劝邓娟放手,最终几乎是把女儿的尸体从她手上扯开。
等殡仪馆的车开出去,宋大姐才发现,邓娟手上拿了一封沾着血的信,似乎是刚才从芬芬衣服里拿出来的。
就一张巴掌大的纸,邓娟几乎看了一晚上。
宋大姐没敢要来看,只怕邓娟想不开,也陪了她一晚上。
不知过了多久,邓娟忽然把信折起来,告诉宋大姐说,她要离婚。
宋大姐错愕地问她,早劝你离婚你怎么从来不听?
邓娟说,那时候马成功威胁她说要是敢离婚,他就把芬芬打死,让芬芬跟他陪葬。她不敢离婚,是为了芬芬。
但她没想到,芬芬会反过来觉得自己拖累了妈妈,她死了妈妈就自由了。
现在,她必须离婚,那是芬芬拿命换来的,她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芬芬。

邓娟铁了心要离婚,这让马成功始料不及。
他更加疯狂地殴打邓娟,咒骂声响彻了小区。
邓娟一句哭声也没有,反而是马成功一边打,一边哭着求她留下。
邓娟强硬地直接搬出了家门,带着几件衣服住进最便宜的女子宿舍,条件好的二十元一晚,差的五元一晚。
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,就去睡地下通道。
那是十一月的西北,滴水成冰。
她还找了宋大姐去做证言材料,证明这些年家暴的存在。
那是宋大姐第一次参与这种事情,她答得特别认真,满心相信自己能帮到邓娟。
但那天的结果,我们都知道了。
由于没有家暴实证,邓娟在法院没能成功离婚。接着,马成功把邓娟抓上了车,最后一次向她挥起了拳头。
从邓娟的家人、芬芬的老师朋友、宋大姐、当时接到扰民报警的警员,到法官、小孙和我,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再较真一点,这对母女都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
芬芬拼了命给妈妈的自由,就这样熄灭了。
一切又回到了马成功身上。但这一次,除了我还有小孙。
小孙是本地的警察,认识的人更多,他联系了一大堆线人,找到了马成功的一个酒肉朋友。
这个线人告诉我们,过几天他们有个兄弟二婚摆酒,按照马成功讲义气的性格,肯定会去捧场。
我和小孙在忐忑中等了三天又三天,生怕马成功不会露面。
终于到了摆酒席的日子,马成功西装革履、人模狗样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我直接上去把他掀翻了。
直到脸被按在地上的最后一刻,马成功还在挣扎着说,这是他兄弟的酒席,喜事不要给冲了,有什么事带他出去说。
我驳斥他:“你他妈知道对别人好,怎么不对你老婆孩子好点。”
他随礼的份子钱是两千。
我问他,知不知道这两千,可以让邓娟在医院里多活两天。

案子移交检察院的时候,我坚持要把故意伤害和虐待罪一起起诉。
故意伤害罪是给邓娟的,虐待罪是给芬芬的。
一对母女,拼了命想要把彼此救出地狱,最后却悄无声息地死去。她们谁都不能没有姓名。
检察官没有把话说满,但我知道,他肯定是当事情办了,因为不久之后我就收到补充侦查提纲,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查证虐待罪的相关犯罪事实的。
这里面也包括我一直在寻觅的芬芬的遗书。
马成功矢口否认这封遗书的存在,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
宋大姐说邓娟没有给她,应该是自己收起来了。
邓娟逃出家门后四处流浪,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小包裹,去法院开庭那天就带在身上。
人被马成功丢在医院时,东西也被扔在医院门口了。
医院把包收到了保卫室,邓秋生去接人的时候并不知道。一直到我再去追查这包东西的时候,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。
中间有一次卫生检查,包裹被放在了保卫室外面,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几个月后,连那天的监控都已经被覆盖了。
我拿到手续后,又闯进马成功的家里搜了一遍,整个屋子里关于芬芬和邓娟的存在全都被清除干净了,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剩下。
芬芬的房间已经成了一个杂物间,没人知道她来过。
我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封遗书。
马成功的案子拖了很长时间,庭审前会议的时候,法官告诉我们还是只能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判,顶格也就十年。
我听说了这个结果,气得一句也不想再问了。
很快,我因为工作原因调离了西北,这个案子就像心病一样困扰了我数年,我几次摸起电话想再问问,但始终没有勇气。
直到今年我想起要记录这个案子,上网查了当年的判决,才发现在我走后,检察官仍然在抗争,最终结果如下——
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,两个罪名赫然在列,无期徒刑。
到这一天,我才敢去想,我其实是愧疚的。
我总是安慰自己,程序上我们都尽力了,但是我们的尽力,比起芬芬,显得那么冰冷。
她才那么小,选择的方式也那么幼稚,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收场。
可她真的以为这样就能给妈妈自由。
但愿世界上不要再有孩子,为妈妈写下这样一封遗书了。

关于这种门内的家暴,陈文章只有一个建议:报警。
你可以坚持按暴力案件处理,让对方进去蹲几天;也可以要求伤情鉴定,保留证据用于离婚。
除此之外,陈文章还总结了几条被家暴后取证的小技巧。
发生家暴后,首先要保证安全第一,减少正面冲突。
1、报警后,要让警察写清楚是家庭暴力事件,而不是家庭纠纷。
2、保留向妇联、社区的救助记录
3、拍照录音录像保留伤情证据,拍清楚伤口,拍好全身或半身像,证明受伤的是自己的同时,不要擅自剪辑,及时去医院验伤。
4、对方的认错悔过书、证人(孩子、亲戚、邻居)等,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保护你、争取离婚的有力证据。
最后,陈文章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有效的建议——
如果你听到有人正在家暴,就去敲敲对方的门,让对方知道外界有人,并且听到他们的暴力行为了。
这源于国外的“敲门运动”,有研究表示,遇到家暴敲个门,有可能制止暴力发生,救受害者一命。
妇联曾有数据,中国家暴致死占妇女他杀死因的40%以上,而每年有15.7万妇女自杀,有60%都是家庭暴力导致的。
所以需要你我伸出援手。
这和陈文章以往记录的穷凶极恶的凶杀案不同,但我却觉得它同样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
每当多一个人能看到陈文章留下的提醒,也许就能多响起一次敲门声。
也有更多“马芬芬”和“邓娟”得救了。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编辑:卡西尼 小旋风
插图:徐六耳
来源链接
|